赵明自述在北京团河劳教所遭药物损伤经历(图)
 赵明曾在团河劳教所受迫害 |
我从团河劳教所被释放后回到爱尔兰两年多了,现在我在爱尔兰持难民身份,硕士论文已经完成,正在找工作。
从劳教所被释放两年多了,我现在两腿下部还是一直感觉麻木,两脚走路多了还痛,我一直以为是在新安劳教所有一段时间“军蹲”体罚导致的,后来回忆起一些事,我才意识到其中很可能有神经损伤药物的原因。
对于我在中国时所遭受的迫害,我一直以来谈的都是我所直接经历、亲眼看到的、明确发生的事,许多都是有很多证人可以证实的,将来迫害结束了,这些事都可以取证,我也没夸张的讲过什么,我讲的在法律上都是切实的证据。其实还有一些事我一直没讲,比如说,我在团河劳教所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可能曾被通过食物施用精神药物,这种事不象被殴打那样是我直接所见,所以我就一直没讲,但我回忆起来,还是有很多线索,所以我现在把它讲出来。
我在新安劳教所被体罚是在2001年4月底、5月上旬,那时在我一年劳教期结尾,新安劳教所恶警加重了对我的折磨,腿脚的麻木感就是那时的长时间军蹲体罚导致的。后来我被延期了,2001年5月19日我被转回到团河劳教所,后来有一段时间,腿的麻木感没那么严重了。可是到2001年底、2002年初,又感觉下腿和脚部的麻木突然又变得严重了,但那时我并没有被体罚折磨,这是很奇怪的事。
2002年新年前,我被隔离了,在团河旧西楼的一楼单独关押,有人24小时盯着我。在这种隔离环境下,如果在菜里加入什么药物,我是根本不可能知道的,那菜总是做的极咸。那期间有过一次呕吐的经历。那是刚到旧西楼没几天,一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翻身,胃里难受,最后感觉吃的东西往上返,恶心,我起来到厕所一下就把晚上吃的东西都吐了,吐完就不难受了,睡着了。我炼法轮功以后胃很好,那天也没吃什么特别的东西,所以这种呕吐很奇怪。

恶警强行灌食
记得2000年6月底我在“七处”被关押的时候,我绝食绝水,七处的医务室主任给我灌食,犯人们叫他“兽医刘”。一天,他叫了一大帮警察十来个,在医务室站了一圈,把我按在中间的地上灌食,他在旁边桌上把一些药片碾碎,说是给我准备营养液。他准备好了“营养液”,用很粗的一个大注射器灌了满满一注射器,开始插鼻饲管,我坚决抵制,我不停的使劲的呕,这样管子插到食管一定深度就插不进去了,再插就从嘴弯出来了。他就拔出去重来,把我鼻子捅出了很多血,最后很多次也没插进去,他气急败坏的说:“往里打,流也能流进去点。”就这样,鼻饲管刚插在食管半截,他们就用注射器往里注射“营养液”,结果绝大多数都被我吐出来了。那液体很苦,不知他里面和了多少药片,但我什么病也没有。我回到号里后,一次一次不停的呕吐,其实我一直在绝食绝水,胃里什么也没有,就是流进去的那一点“营养液”,吐出来的西药味极大。人们都知道,很多西药是不能空腹吃的,就是因为对胃的刺激极大,我什么病也没有,在我几天食水未进的情况下,他给我灌这么浓的药液,就是要折磨我,真是够恶毒的,幸好我抵制着他没灌进去,只是流进去一点,要是真的灌进去了就惨了。
所以我觉得在团河被隔离期间的呕吐可能是食物中的药物导致的。2002年初,我腿脚的麻木感越来越严重了,我跟警察说了,2002年2月左右,他们带我到劳教所附近的团河医院做外科检查。医院的大夫拿一个金属的不带刃的刀状的器具轻触我身体各处的皮肤,一触,就会引起皮肤的抽动反射,这样来检查皮肤的神经功能。因为是检查身体前侧,我一直看着他检查各个地方,我吃惊的看到当他触我的大腿根腹股沟附近的时候,我的皮肤没有反射!大夫反复检查了几次,我记得他问了我至少三次“你大小便能控制吗?”我说“能控制”。我虽然大小便能控制,但确实有不正常的感觉,就是我感觉肛门和尿道内壁是麻木的,不知道排便排干净了没有。
可是大腿根和排便器官的这些麻木症状当时在新安被军蹲体罚时并没有,这肯定是在隔离期间导致的,而那期间我没有被军蹲体罚,所以这只能归结为吃了损伤神经的药物导致的。而腿脚的麻木感是被这种药物加重了。
我记得小时候看日本电影《追捕》,检察官杜秋以患者身份潜入精神病院调查,被服用神经损伤药物迫害,他每次吃完药就用手捅嗓子把药吐出来,得以保全。可是我完全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无从抵制。好在法轮大法有自动保护修炼者的功能,绝大部分药物都通过呕吐或排便排出去了,要不然我今天就已经变成“横路敬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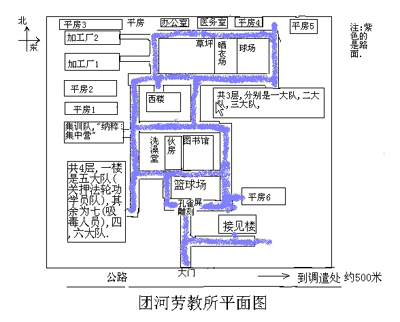
团河劳教所平面图
回忆起来,其实我在团河劳教所被监禁的结尾一段时间和释放后的一段时间感觉非常不好,回到家了也吃不香,睡不着,脑袋木木的,我在劳教所里被折磨得最艰苦的时期都没有那么难受过,那时我沾枕头就着,在鏖战中利用每一点时间休息。我以前曾写文章说,我出来以后感觉情感是麻木的,我一直以为那是洗脑迫害导致的。现在我才想起来,其实那种情感麻木的感觉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精神药物导致的。
那么,在劳教所里用神经损伤药物迫害,这不是一般的警察单独能做得了的了,他们也没有这样的专业知识和药物来源。我想这决不是一般的级别的警察参与导致的,但使用神经损伤药物迫害我的最直接的执行者一定包括在隔离期间看押我的“攻坚班”警察,因为别人无法有机会在我的食物中掺药。
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其使用的手段之邪恶程度上也确实是登峰造极了。现在这些事那些恶警可能觉得都瞒得挺好,其实等江泽民一倒,法律公正能在中国实施的时候,这些各级参与迫害的警察、官员自会相互揭发、转嫁责任,到时都会真象大白。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04/8/17/51448.html



